作者:张伦,安德烈
习已执政两届十年了,我们如果用什么来概括习近平这十年的话,我觉得“大反动”这三个字可能比较好地概括他执政十年的整体的政策取向。这个词大概2014年左右就开始在我脑中浮现,已很久了,前几年我曾出过一本文集『失去方向的中国』,收集了那些年对中国一些事件的分析评论。“失去方向”是对整个中国的状态的概括,从精英到大众都开始给人呈现出某种失去方向的感觉,但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要扭转中国的演变方向,向改革前毛的政策回归的“大反动“必然带来的结果。
说习搞大反动,是因为它跟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主流方向是相反的。文革后启动的改革的基本指向还是朝着自由化方向的,至少在某些方面这自由化改革一方面是权力主导者允许, 鼓励的结果,另一方面不是官方的主观预设,而是中国民众不断以各种方式争取,抗争所造成的。受到党国极权体制压迫的中国人走出毛时代,渴望自由和民主,改变贫困,整个社会开始反弹复苏。上与下,社会和国家,权力精英与知识分子和民众在渴望改变中国当时的现状,获取更多的自由上暂时取得了共识。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等希望这是一个更完整的改革,不仅是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还有政治的面向;但中共中的一些人并不希望有这样一个整体改革,他们希望这是一个威权性的鸟笼式的服务于中共统治集团利益,受中共完全控制的改革,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与所谓保守派的陈云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邓的想法可能更复杂一些,这个鸟笼在陈云那里除党的领导外是计划经济,在邓小平那里是政治威权,是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改革与局部改革两种对中国改革的设想后来在八九时产生了冲撞,中共内部政经两方面反对全面改革的路线合流,对党内外主张全面改革的力量进行清算,这场冲撞对中共震动极大,加之苏东阵营崩塌,中共知道如果不给社会更大的自由空间,自己也难以生存,所以有了邓小平的九二南巡,陈云式的政治加经济鸟笼瓦解,官方全部归结到邓的政治鸟笼路线上来。但可以说,即使发生了六四镇压,社会大体上的演变方向还没有全变,但是因政治踏步不前,经济获得新的空间,两者失衡,协调性全面改革不再,改革进一步畸形化了,经济虽得到发展。“半拉子改革”模式开始形成。
六四之前还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虽因六四破碎,但是大家还存着一个模糊的希望,包括西方对中国也是如此:希望经济改革如果继续下去,也许有一天,自由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的增长,会导致中国出现像台湾、南韩那样的变革。而中共领导层也在玩这个游戏,给你一种可能性想象,给许多人和西方一个幻觉。这也是西方现在在检讨对华关系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面向。事实上,六四之后政治固化靠经济增长却换取了新合法性资源,这强化了中共一些人的信心,要走所谓它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一党专制下的现代化,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模式,所谓“自信”论,“中国模式”论等开始出来,已不仅仅是过渡性的东西,工具性的东西,而是被鼓吹为一个制度性,文明性的新模式。
这有国际国内的背景。零八年之后,发生金融危机,西方经济受到重大挫折。国内的背景就是中国入世后的经济突飞猛进,举办奥运,信心爆棚,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持久下去。等到习上台,认为过去出现的一些问题只是因为邓模式偏了,可以用毛的模式纠正邓的模式,来打造他的模式。我七,八年前讲过我的观察:习要做的就是“毛邓兼用,毛邓互补,打通毛邓”,成就自己的模式。加上这期间,西方内部因各种问题包括全球化的不适带来的后果逐渐显现,有了他所谓的道路自信,“东升西降”,认定自己的模式要独领风骚,替代西方了。
概括而言,他的大反动就是对几十年改革开放主流的一个反动,也是世界范围当下出现的对后冷战时代自由民主大潮的大反动趋势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到了江胡后期,悖论已显,就是到底要不要跃上一个台阶,让中国人能获取更多的权利,公民权利能够有更多的制度化的落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人们某种经济权利的获得。本来中国的改革就是以权利的扩展为起步的,比如小岗村的农民起来承包土地就是一种解放,权利获得。自由空间的增长,公民权利的增加,这是改革的核心。但是到了一定时期就跟邓的威权路线发生了矛盾,就是说他能够放的东西都给你放了,最后到了权利(right )跟权力(power) 开始要发生无法调节的冲突了。这从经济领域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国企民企到一定时候如何协调开始发生矛盾;社会领域的官民利益冲突激化,维稳就出来了,这已经有反动的迹象,但江胡时代还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寻求一些观念与制度性探讨与妥协,比如江的“三个代表”,胡时代的“和谐社会”,甚至官民都还没少提“公民社会”,总之还有一个重建国家与社会以及彼此关系的企图,讨论的空间。
到习的时代,解决国家与社会紧张关系的不同在于:就是不玩这套了!而是用毛时代的东西来解决改革中发生的问题。习的大反动与以往做法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区别在于它是反权利增加的改革,甚至它要削减你已获取的某些自由,更限制你的自由,限制民间公民社会力量的增长,重拾改革前的方式加上新的技术手段来应对不完整改革造成的问题,这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大反动。
如果再来看近代中国历史趋势的话,可以发现其中经历了几个重要反复,中共夺权包括后来的执政经历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民国时代的历史的一个大反动;再往前,清末也发生过几次这样规律性的变化。后文革时代是对毛时代的一个修正,重新靠近世界主流文明,与现代世界、与现代性接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自由,所以中国内部理顺了,也顺应了国际潮流,才有后来的格局。那么,习现在所做的不仅是对这三,四十年的改革整体趋势的一次大反动,同时也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进程中发生的新的一次大反动。这是第二层意义上的大反动;第三个层次也跟此相连,它实际上是对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人类主流文明的一次大反动,这些都是就其政策的反自由的本质性特质来讲的。
关于经济的问题,习在两三天内逆转解封,没有任何章法和准备,固执三年的清零让社会付出巨大成本。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了前三季的经济数据,非常糟糕,这一定是他们最后突然做这个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中共的数据都是政治数据,不可信的,比如为什么有所谓的李克强指数,就是李克强当初本人也说自己不相信中国的数据,用耗电量,货运量及贷款等来加总来分析经济运行真实状况。现在的局面是相当严峻的,一个是你刚提到的人口,一个就是经济,官方公布的数据都那么糟糕,他们内部的数据,实际情况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只能想象。
中国社会,中国人这些年已经为习的政策付出了巨大代价,经济因解封会有局部反弹的,但中国失去了方向;方向有了问题,许多东西就都理不顺了,经济最终也很难搞好。中国要往何处去?再一次成为我们必须要讨论的问题。许多人谈论中国崛起,但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其实不是什么投资,经济数据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可能是中国人的精神迷茫,缺乏信心,对中国将来要走向哪里的困惑?这不是所谓习近平思想所能解决的。回头看后文革时代,邓小平的实用思想其实管了几十年,它有它的功效和历史地位,就是解构毛的那一套东西,有助于人的思想解放,但回避了中国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发展与文明目标的问题,其局限以及带来的问题今天已经非常明显,我们到了一个时候,需要重新定义民族的现代性构建方向,价值标准,这是关键。
这些年,在习看来,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中所具有的自由化趋势有可能最终瓦解中共政权,出于巩固中共权力以及他个人的权力的需要,他要扭转这种趋势,用取消自由的方式来应对因为自由不完整的改革带来的问题。因有了局部自由,中国才得到发展,因自由的不完整,缺乏新闻自由,财产保障,司法独立,选举权利等才让腐败横行,社会不公,这些本来应该用更深刻完整的改革来解决这不完整改革带来的问题,但习近平的解决之道是是用改革前毛的方式,重提党的绝对领导,焦裕禄、雷锋,倡导红色基因教育等等,导致整个社会陷入迷茫和无所适从,从精英到普通人,许多人都很困惑,包括整个华人世界都被搅得很乱。这个状态持续下去,就与西方的关系来讲即便因各种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有局部暂时的缓和,但也不可能有根本的缓解,因为那不仅有利益,更是价值上的冲突。模糊的空间不存在了。中国的各种问题很难从根本上理顺。还会继续让中国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威权甚至极权的“模式”都可能在某种条件下造成经济的增长,希特勒治下的德国经济高速发展,民众也曾得到过很多的福利,因此万众欢呼;苏联也出现过经济高增长的时期,但是制度与价值性的问题不解决,文明的方向性不解决,将来可能是眼看着它大厦起,也可能会看到大厦倾的。
他的中国梦,复兴中华,恰恰因为他的做法很可能最终使中国远离这些目标。毛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饿,几千万人中国人死亡,习清零三年的行为决策方式跟大跃进三年类似。毛失败后暂时退居二线,最后发动文革反扑。而习的个人声望因三年清零受损,在中共党内一定也会有反映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做一些适当调整。但我的问题是,他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什么问题上发动政治反扑?台海问题是否是一个可能?当然现在的情况与毛时代相比也有些不同,一方面是因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受到的制约更大;但另一方面麻烦的是习近平也可能更少一些元老们的掣肘,决策的不确定性也大增。没有平衡调整的体制,本来有一个到点退休制,给中国这二三十年带来政治上的某些稳定性。可预期性。现在取消了,什么都全系一身,极大地增加了政治不稳定性与不可测性。领导人退休制让社会如果有不满还有一种盼头,现在习近平让社会失去这种可能,其实社会的绝望情绪是白纸运动发生的另外一个深层的社会心理原因。
在这样一个比较暗淡的时期,一些未来的征兆很可能已在孕育。白纸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它象征着年轻的一代重新开始站上历史舞台,这是三十年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意义极其重大。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抗争没有断过,但基本上是在社会,经济诉求层面,政治层面的尤其是在街头的政治诉求是没有过的。我曾经跟年轻人说过,中国的现代性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哪一代人都会摊上事。某种意义上说,过去二三十年度过青春期的算是幸运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可以旅游、留学,玩自己的,未来可期。与我们那时代一个重大的不同是,那时政治和我们的生活是连着的,我们受苦跟毛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与个人生活开始慢慢有些分离,六四之后,中共有意放松一些,你愿意吃喝玩乐没关系,只要你不问政治我就不管你。习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三年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这个权力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政治的压迫性重新跟现实的生活又发生连接。政治高压、经济滑坡、青年失业率很高,习近平第三次登基,个人前途迷茫。于是,政治问题,权力问题,公民参与社会的政治问题三十年后又复归,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这就是这次白纸运动最深远的意义。躺平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抗争”,走向街头是另一种抗争,其实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永远躺平的,从躺平到街头,或许就是一念之间。问题意识重新出现,政治性口号提了出来,又开始与三十年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要求法治、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基本诉求衔接。路还很长,但是基本问题重新提出来让人们思考,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这个疫情肆虐,经济下滑,权力暴虐的黯淡的时光大反动时期,社会依旧在抗争,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抗拒这个大反动。
我曾经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概括为一个从改良到革命,再从革命到改良的巨大历史循环,晚清末年改革,没改革彻底闹出了革命,因各种因缘一直到共产革命,文革,一波高过一波,然后出现大转折,再开始改革,现在它又有了一个大反动,改革陷入死亡。中国将来怎么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需要一种新的“革命性改革”,来完成或终结中国近代以来大的轮回。
“革命性改革“就是要突破体制,改掉现有模式,但尽量避免以传统型的大规模流血的革命方式,把改革目标彻底重新设定,以公民的权利增加及其保护作为改革最重要的标准,将中国的“文明崛起”作为目标。关于如何做到能否达成这些问题以后找机会再详述,这里简单先提这么几句。这些年,说了许多中国崛起,外国人也说,中国人也感到自豪,但我认为中国人现在需要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崛起的方式以及最后的目标是什么。近代以来,出现过日本式崛起,德国式崛起,结果给自己民族也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崛起于世界之林,无可厚非;人都有上进争强之心,要受人尊重,人之常情,但怎样崛起才是恰当的,崛起为了什么才是需要考虑的。想超过美国,可以,但你要怎样才能做得比美国更好?美国现在有的某些东西应该是中国汲取的,同时美国不足的东西我们要能够做得比它更完善,这个才是中国人应该努力要达成的目标。就当下讲,如要抗拒大反动,就要有一个关于未来的方向。习近平现在这个大反动的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民族主义。跟毛时代有所不同,毛时代还有一些乌托邦的东西,他现在抽掉乌托邦,用彻底的民族主义加上毛的另外一些专断的东西来展开大反动。我们应该用“文明崛起“来消解习的民族主义崛起,作为努力的方向,中国人将来可以在文明的创建上,更新再造上,与他人竞争,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但这又不是习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个东西抽空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要素。中国人要汲取过去自己与他人的教训,文明崛起的核心就是首先把现代性中最基本的关于自由、人权、民主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在这基础上结合自己民族的文化对现代性加以补充或发展,再创造。这个方向要确立,要有一些新的思考,以抗拒习主导的这样一个大反动,才有可能减少中国人自己遭受灾难且给他人带来灾难的可能,这个民族将来才有可能真正在世界上赢得荣光,实现对自身及世界都有利的崛起。
以上摘编自RF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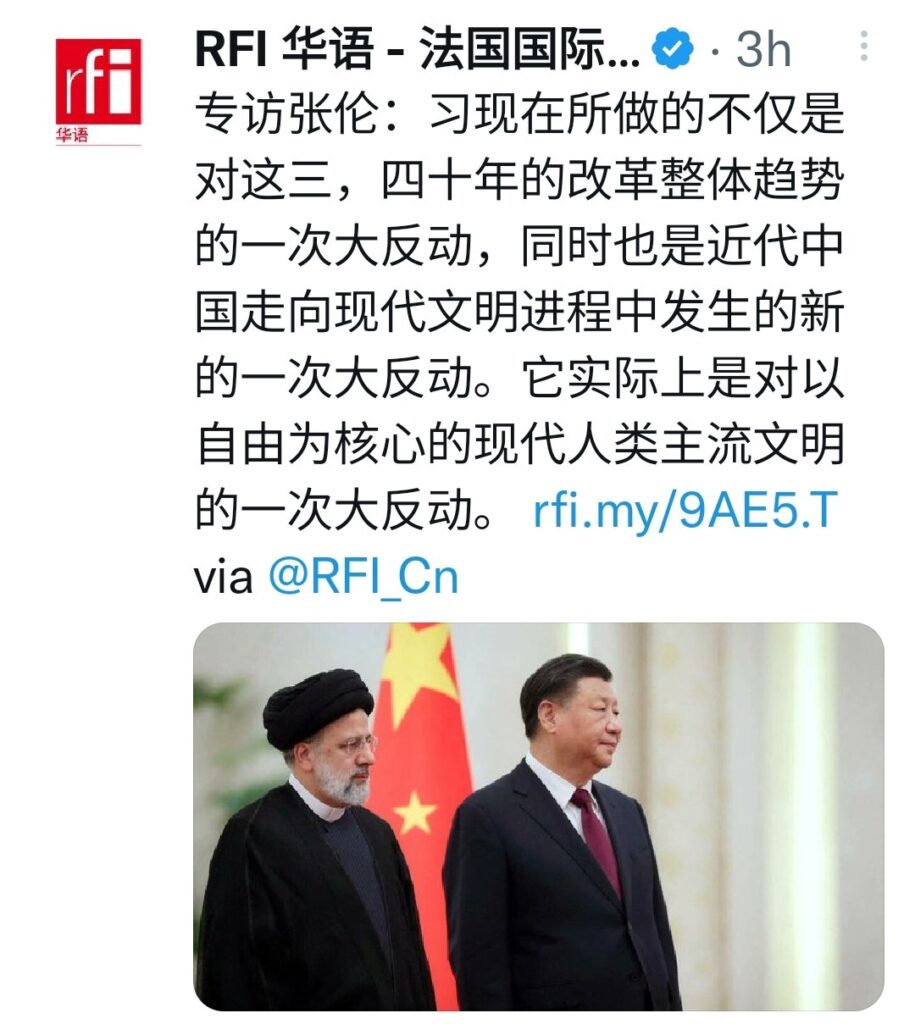
专访张伦:习近平的“大反动”与中国的“文明崛起”,作者,安德烈
张伦,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先后在沈阳大学、北京大学学习经济与社会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从师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获博士学位。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会走向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