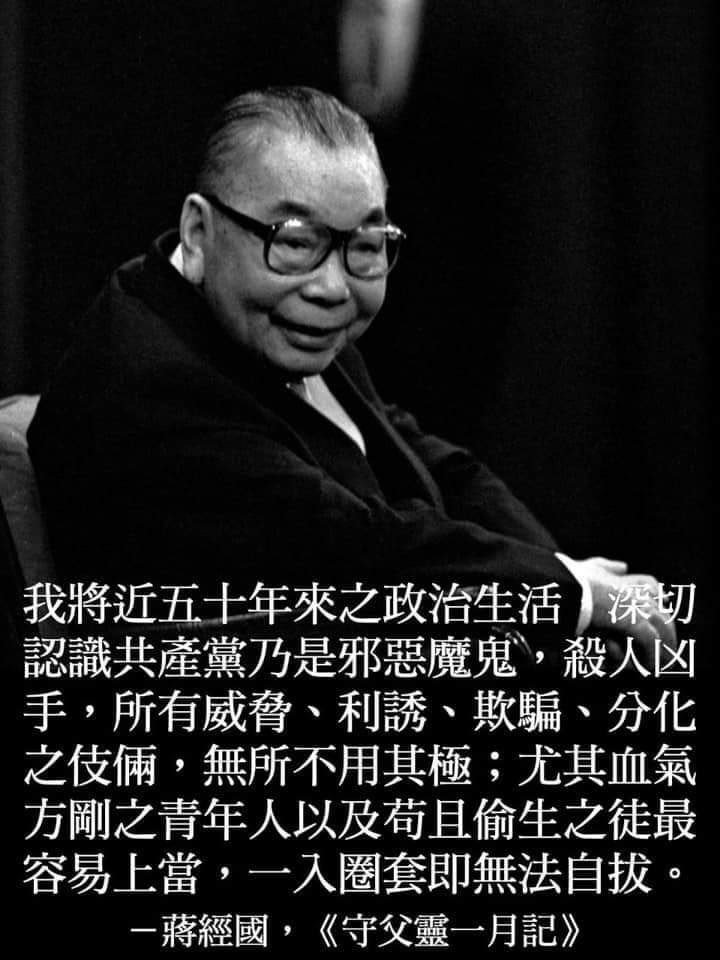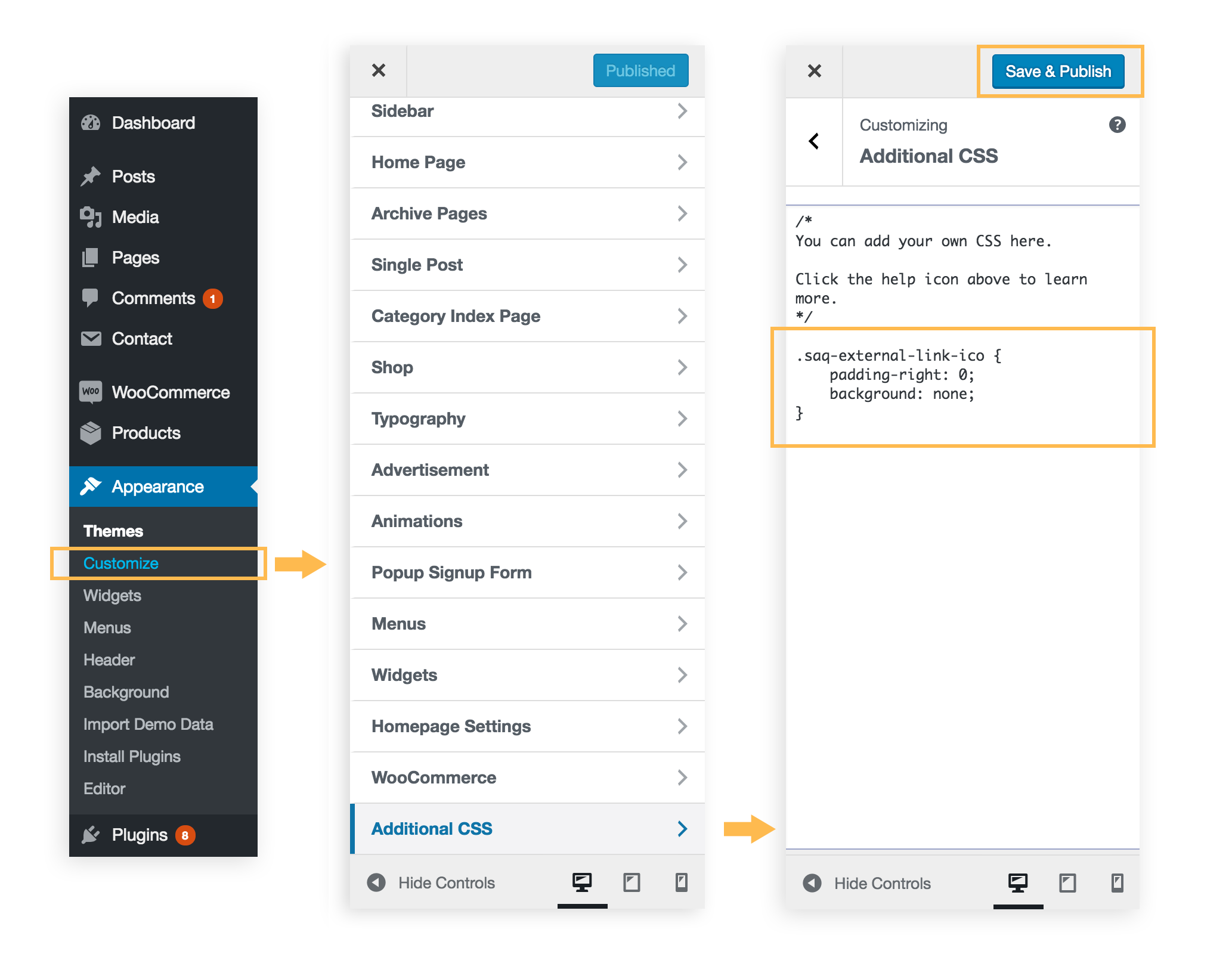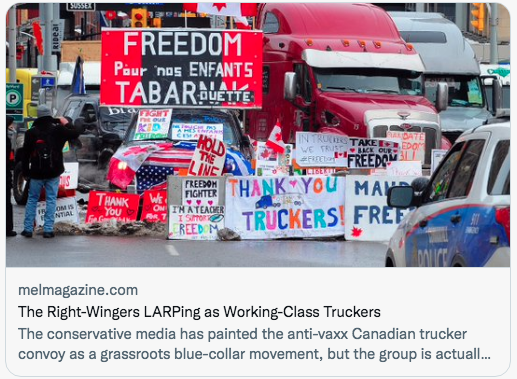现在西方有些学者批评马克思主义,说它是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这不无理由,却又失之简单化。
现代西方有两大思潮,一是经验主义,一是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故乡在英国,代表人物是洛克;理性主义盛行于法国,代表任务是笛卡尔。经验主义注重搜集个别的、特殊的事实,而不大急于发现普遍规律、建立庞大的体系。在政治上则表现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改良主义。洛克也是自由主义政治理想的代表。
理性主义则一开始就探求绝对的、普遍的、无可怀疑的、颠扑不破的真理,醉心于构造包罗万象的体系。
1994年在美国时就看到报章上对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介绍,很想找一本来看看。回国后买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其中就包括这篇著作,很高兴,一口气看完了。
顾准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恐怖条件下写下了这些文字,到今天仍然闪现思想的光芒。我钦佩他的勇气和独立精神。特别是,那个时候他就看到“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中发现了‘异化’的秘密,他认为不可能在哲学中解决异化,要在经济学中解决异化。这就是《资本论》的哲学前提。价值,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剥夺者被剥夺,这就是在经济学中解决哲学上提出的异化的道路。”寥寥数语,就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的思路。这种对马克思的深刻理解,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他对唯理主义思潮对革命学说的负面影响,也做了很深刻的批评,这对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在当时,这应该说是一种创见,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惜过了二十年才出版。
如果考虑到作者在生前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些写给弟弟的讨论问题的家信竟然能出版,那么这本书的某些论证缺乏严密性就不奇怪了,对此我们也不能苛求。然而,我还是想对这本书中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的部分发表一些评论。我将先做正面的阐述,然后在来考查顾准的批评。
理性主义的时代
欧洲的17世纪是理性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由笛卡尔开创的。
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开始。一切都可以怀疑,但“怀疑”这件事本身不能怀疑。我怀疑,说明我在思想;我思想,说明我存在。这就是笛卡尔的有名的 cogito , sum(我思故我在)。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思想”是“我存在”的原因,我先有思想然后有存在,象许多人误解的那样(因而这句话成为笛卡尔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证据),而是说“我思想”是我做出“我存在”这个判断的根据或理由,我必须先有存在然后才能思想。笛卡尔把“清楚明白”作为真理的标准,“我在”是最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事,所以它是真理。对笛卡尔来说,怀疑只是手段,他的目的是达到真理。
笛卡尔的这个“我”,是一个思想的主体,是一个理性的我。
追求确定无疑的真理,是理性主义者的最高目的。他们从数学得到启发。在数学中,一切是那样天衣无缝,绝对完美,那么,为什么哲学不能以数学为榜样呢 ? 哲学能不能也从少数自明的公理出发,依靠严格的逻辑推理的办法,一步一步导出许多原理来,构成一座巍峨的哲学大厦,解开宇宙之迷呢 ? 这是理性主义者的梦想。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无非是要使这象几何学中的公理“两点间直线最短”一样,成为一个出发点,推导出一系列其他基本原理来。
笛卡尔之后的另一个著名的理性主义者,德国的莱布尼兹,相信整个宇宙都是合乎理性的,受必然规律支配的,是有一个严整的秩序的。如果人有上帝那样的智慧,他就可以用纯逻辑的方法推演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变化来。
理性主义又非常相信个人的理性,用理性来衡量现实,因此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理性时代之后是18世纪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角是法国启蒙学者和百科全书派。他们在现实中处处看到不合理,因而要求改造现实,使之和理性一致。政治上,理性主义则表现为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理性成了真理的标准,合理的就是真理,而合理就是合乎理性。于是,这些思想家就用理性的尺子来衡量一切,批判一切。
“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3卷,56-57页))
这是一个对理性充满幻想的时代,黑格尔这样描述了当时人们的心情:
“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可萨哥拉第一个说,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知道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
法国启蒙运动也影响了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利叶、圣西门。
法国启蒙运动、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和黑格尔哲学,都是在理性主义的大潮流之中。那么,继承了这些思想的马克思,是否也继承了它们的理性主义呢 ? 如果继承了,又是怎样的继承呢 ?
从形而上学的理性到辩证理性
在回答这个这个问题之前,先要简单回顾一下哲学史。
第一个对理性提出怀疑的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他认为“道德准则…不是我们的理性的结论”。(4页)象道德一样,理性也是一种进化选择过程的产物(24页)。
休谟给理性主义泼了一瓢冷水。他指出,事物的因果关系不是逻辑关系,一个原因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只能从经验中得知,不能从逻辑上推演出来。
休谟的论证惊醒了康德的“形而上学之梦”。经过多年的苦心潜思,康德在1875年写出了他的划时代巨著《纯粹理性批判》。
这本书给形而上学以沉重的打击。康德指出,虽然理性是人的认识能力,但是它是受到限制的,它不能超出经验以外。一旦越出经验的范围,去研究超经验的事物,理性就会陷入“二律背反”的谬误。过去的形而上学正是要去研究什么上帝、灵魂、自由意志等,所以就没有任何结果。
休谟启发了康德。康德限制了理性,认为理性不能应用于经验以外的事物。过去的形而上学以为靠纯粹理性能够认识上帝和宇宙的本体,结果陷入不能解脱的矛盾或“二律背反”,其原因在理性的误用。上帝是信仰的对象,不是理性的对象。
黑格尔又批判了康德。康德说用理性认识“物自体”就会陷入矛盾,这说明理性的无能。黑格尔说,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世界本身就充满了矛盾。过去的形而上学者的错误,不是因为陷入了矛盾,而是他们以为矛盾只存在于主观之中,矛盾就是谬误。问题不在于限制理性,而在于批判形而上学的理性,代之以辩证的理性。这个辩证的理性不仅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而且弥漫于万事万物,不仅如此,它还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一切变化的推动力量;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理性”。
中国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么大的问题,几句话就对付过去了。黑格尔不然,他写出了一系列的大部头著作,给我们证明:绝对理性是如何从“有”这个正题出发,走到自己的反题,即“无”;“有”与“无”又如何融合成为“变”这个合题。如此等等。这是绝对理性的逻辑阶段。逻辑阶段发展到反面,就是自然。自然界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出现了人,于是进入精神阶段。精神是逻辑与自然的合题。精神又有三个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完成了。所有这一切发展,都严格的依照辩证法的三段式:正、反、合;或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通过把形而上学的理性改造为辩证理性,无限地提高了理性的地位。他的“绝对理性”,成了哲学化的上帝。这样,黑格尔就犯了和以前的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者一样的错误,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
从唯心辩证法到唯物辩证法
这种僭妄的态度受到了费尔巴哈的批判。费尔巴哈说,既然依照辩证法,一切哲学都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那么黑格尔哲学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和局限性;怎么能说黑格尔哲学是超越时代的绝对真理呢 ?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又批评黑格尔没有把辩证法贯彻到底。恩格斯指出,按照辩证法,发展永远不会终结,但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者,又要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而一个体系必须有一个终点,宣布它完成了对绝对真理的认识。这是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的矛盾。
恩格斯也用辩证法的观点来批判法国启蒙学者了理性主义。他指出:一切都是发展的,真理也是发展的。没有停滞不变的事物,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义,没有穷尽一切的真理。甚至理性本身也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法国启蒙学者自认为他们代表普遍理性和永恒正义,其实他们的理性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已。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这要看具体的历史情况。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合理的奴隶制,在历史上却曾经有它存在的理由;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它才失去了合理性,从而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新的社会制度在现在是合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退移,它会在将来变成腐朽的、不合理的东西,从而让位给更新的制度……
但是,“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是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有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恩选集》4卷212-213页)
这说得十分明确: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赋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相反,他们批评了任何这一类的看法。
然而,并不是把理性看做是发展的东西,问题就解决了。
黑格尔对理性持历史的、批判的态度,这是他和18世纪思想家不同的地方。但是,黑格尔是用理性批判理性,这种批判是理性的自我批判。理性不断展开自身的矛盾,又不断通过批判而扬弃这种矛盾,达到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如此循环往复,理性就通过这种辩证的批判而不断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的是理性和现实的矛盾和现实之中的矛盾,不仅用理性来批判现实,还要用现实来批判理性,对现实的批判也不是限于理性批判,更重要的是用革命的实践来批判。这又是马克思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同的地方。恩格斯在评论空想社会主义者时说:“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马恩选集》3卷,58-59页) 。这是唯心的观点。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改变世界。至于社会和历史的规律,这不能象黑格尔那样从头脑中推演出来(即使是用辩证的方法),而应该从现实的运动中发现出来。这是把唯心的辩证法改造成唯物的辩证法,这样也就否定了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一词有多种含义。广义地说,理性主义是指一种尊重理性,尊重科学,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和迷信,凡事要问一个“为甚么”的批判精神。这种意义的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拒绝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即认为理性可以不依靠经验的帮助,单凭自己的力量来认识真理,而且这样达到的真理才是最可靠的。这种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一个不同点是,经验主义哲学往往没有什么严整的体系,而理性主义者却把建立体系看成是哲学的生命。
当恩格斯宣称“哲学的终结”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指那种以发现绝对真理为目标的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他说那种包罗万象的、凌驾在具体科学之上的哲学再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它们要随着黑格尔哲学的终结而成为历史。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并不说这也是一种哲学,只是说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基于上述,应当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绝没有自以为发现了绝对真理的。
绝对真理和不可知论
我感到遗憾的是,顾准撇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而找出片言只字来证明他的观点。
顾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批评是:它主张绝对真理可以认识,这是它的根本错误。顾准认为绝对真理是永远不可认识的。绝对真理之所以不可认识,因为人的一切认识都来自经验,而经验永远是有局限性的。他把这种观点称为唯物论的,因为它坚持一切知识来自经验。他又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不可知论”,因为它认为人的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绝对真理。
作者对“不可知论”一词的用法,显然和习惯的用法不一样。但是这里除了这个词的用法不一致以外,在实质上,作者所主张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歧在那里呢? 难道恩格斯、列宁没有说过同样的话吗?
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相反的观点,顾准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如下一段话: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他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他的个别实现和某一时候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顾准从这里推断说,恩格斯的意思是“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并认为,这里隐含着人的潜在的神性(《顾准文集》,404页) 。
如果看一下上下文,就会明白,恩格斯所针对的是杜林的狂妄自大,宣称终极真理就在他的手里。恩格斯当然否认任何人可以完成对绝对真理的认识;他也曾这样批评过黑格尔。但是恩格斯也企图避免另一种片面性;他想解释认识的两重性。任何个别的人都不能穷尽绝对真理,但是人类总是在无穷地接近绝对真理。任何时候人的认识都受到限制,但任何时候人的认识都不会遇到“到此为止,不得逾越”的雷池。我想这就是恩格斯想说的意思。还要看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不是可以绝对分开的,相对真理中就有绝对真理的颗粒,这就是后来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所作的发挥。如果说恩格斯有“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的意思,那就要说,这种可能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人类的历史可以延长到无限。但无限长是不可能的,恩格斯也谈到过人类和地球的灭亡,所以实际上人是不能掌握绝对真理的。
恩格斯提出过实践是人的认识的检验。顾准提出异议说,实践证明了的不等于就是绝对真理;这是对的。但恩格斯的意思并不是说实践证明了的就不能补充和发展了。列宁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实践的标准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这和恩格斯说的人的认识的至上性和不至上性的意思是一样的。
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关于人永远不能掌握绝对真理这一点说得十分明确:
“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马恩选集》4卷212页)
顾准也引了这一段话 (《顾准文集》,407页),但是他没有予以重视。他认为,到写《费尔巴哈论》时,恩格斯变了,在写这些话的时候,“真可以说竭尽一切力量来遮盖‘辩证法=神学”的性质”(《顾准文集》,411页)。唯有极其细心的读者才会发现恩格斯在“反对不可知论,亦即在十分委婉地主张唯理主义。”(《顾准文集》,411页)
恩格斯反对不可知论的立场是明确的,但是反对不可知论不等于主张唯理主义。顾准把“不可知论”了解为绝对真理不可知,因此谁反对“不可知论”,谁就是主张可以掌握绝对真理。作者自居为“不可知论”,他说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
“至于不可知论者是唯物主义者,只是它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坚持他所知的事物的特性,是这些特性对感官产生的印象,而不肯进一步认为,这是‘绝对真理’,这对严肃的科学工作来说,有什么不好呢 ? ”(《顾准文集》,423页)
作者对“不可知论”一词的用法,显然和通常不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不可知论”是指拒绝对认识的来源做出回答,在唯心和唯物的争论中采取了中间立场。康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如果顾准认为一切认识来自经验,同时又否认这个认识是绝对真理,那么他并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唯物论者。不可知论之所以是不可知论,并不是因为它拒绝认为他所知的事物的特性是绝对真理,而是由于它认为人所知道的只是经验,至于经验从何而来的问题,或经验以外的事物的问题,我们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知识的。坚持认识来自经验,不一定就是唯物论,因为还有一个如何解释经验的问题,经验从何而来的问题,因此才有贝克莱那样的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者。顾准说人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来自事物的特性,其实这句话已经超出纯粹经验的范围了。不可知论者不可能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因为他回避了唯心唯物的问题。象马赫一派的哲学家看来,无论是进一步认为经验的本源是物质还是精神,都是超出了经验的范围。顾准把他们说成是唯物主义者,是很奇怪的。他说经验批判主义其实是康德主义清除掉不少宗教成分以后的东西(《顾准文集》,425页);他没有提到的是,这一派也清除掉了康德的“物自体”。
“不可知论”(agnoticism) 这个名词是赫胥黎在1869年首先使用的,胡适曾译为“存疑主义”。赫胥黎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帝、灵魂一类东西存在;关于上帝的存在问题,既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证据否认,只能存疑。后来这个词被移用到休谟身上,因为他认为经验以外还有没有实体(无论是心还是物)存在是不可知的;也移用到康德身上,因为他认为虽然可以肯定物自体的存在,但它是不可知的。列宁认为不可知论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派别,这是对的。既然是动摇,就可以偏于唯物(赫胥黎),可以偏于唯心(马赫),也可以居于中间(康德)。不管怎样,把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等同于不可知论,是不适当的。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应当是培根和洛克,他们不是不可知论者。
唯理主义和辩证法,辩证法和神学
顾准对唯理主义(理性主义)一词也有他自己的了解,不顾哲学史上存在着反辩证法的唯理主义的事实,他把这个词等同于辩证法,而辩证法又等同于神学。
他认为这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下来的遗产。“从哲学上来说,到此为止的唯物论都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则是唯心论的。现在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了。不是称做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吗 ? 按照上面我们对辩证法本性的描摹,把它译成唯理主义的唯物论,显然是顺理成章的。”(《顾准文集》,413页) “这一结合的后果是异常巨大的。从政治上来说,它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同上)
顾准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神学,还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绝对完美的社会,和绝对真理一样神圣的东西。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论证的,这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顾准认为唯物论和辩证法不能相容,也就是不能和唯理主义相容。主张辩证法,就意味着主张唯理主义,而主张唯理主义就要陷入唯心主义;要避免唯心主义,就只能坚持经验主义。这个说法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只能在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择一。难道就不能把经验和理性结合起来,把两者各放在适当的位置吗?
顾准之所以认为辩证法是神学,还因为辩证法提出了宇宙的普遍规律。他诘问:“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吗? ”他认为,一切知识只能来源于对经验的归纳,而经验永远是有限的,因此,“凡是你从客观世界观察的来的规律,总不过是或然的规律,决不是必然的规律。”(《顾准文集》,421页)你哲学家有多大能耐,能观察宇宙上下古往今来一切事变,断言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 这种断言岂不是把自己看做是神,而把辩证法看做是神学吗?
但是一切科学都要探寻规律,没有规律就没有科学,而一切规律都是有普遍性的,不过是普遍性的范围和大小有不同而已。顾准的诘问适用于一切科学。就以“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这个物理学的规律来说吧,你物理学家有多大能耐,能观察宇宙上下古往今来一切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断言你已经发现出来这条规律是普遍的,没有例外的呢?
“真正的,首尾一贯的唯物主义,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即一方面承认人的头脑(心智)可以通过观察、直观、实验、推理等等一切方法来了解事物的过程,做出各种各样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妥当性限制在哪个范围,其或然率是高是低,唯有事实才能加以验证。”(《顾准文集》,422页)
但假设又是什么呢? 难道假设不是理性的产物吗? 难道不正是因为经验不够用了,才需要假设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波普尔的否证法:一切科学的规律之所以是规律,就因为它是可以否证的。这样一来,说到底,规律和假设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关于“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这个原理,顾准解释说:“这能做这样的解释 :(一)历史按照逻辑的必然性而发展;(二)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什么 A=A 、判断、推论之类的‘思维规律’,而是中国人所谓的‘道’。‘大道之行也’的‘道’,是先验的东西。”
顾准援引马克思的下面的话来说明马克思的唯理主义或唯心主义: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 . 跋》)
作者说:这段话作为他的评论的“正面证明微嫌不足,不过也可以嗅出‘道’的强烈气味来”。
其实,这里和“道”不相干。如果看一看上下文,就会知道马克思区别了“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资本论》有它的逻辑结构,从分析商品开始,从一对矛盾过渡到另一对矛盾,又到第三对矛盾,一环扣一环,层层深入,看起来好象是纯逻辑的推导。马克思深恐引起误会,所以特地申明说,这只是他的“叙述的方法”,而不是“研究的方法”。在实际研究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并对它进行分析。这就是从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出发”到哪里去呢 ? 到规律,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各种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和生命。一旦找到了这个,在叙述时,就可以用观点来统帅材料,于是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其实并不是。马克思强调说,这是他和黑格尔的区别,后者认为理念是世界的创造主。
这也就是“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这个逻辑就是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在黑格尔那里是先验的东西,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不是。马克思不是要将逻辑强加给历史,或把历史纳入逻辑,而是要在历史中寻找出逻辑的必然性。
“历史和逻辑的一致”的提法是否适当是可以讨论的。我记得好象王元化先生也提出过质疑。我只是说,象顾准那样简单地论证恐怕是不行的。
杜林说马克思只是依靠“否定之否定律”来证明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的,恩格斯在批驳这一点时,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把辩证法当做先验的东西而强加给历史事实,他说:
“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象以往小生产者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
“……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马克思并没有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必然性。”(《马恩选集》 3 卷 173-174页)
缀语
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批评,是说理性主义给了马克思主义以负面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了空想的成分。近十几年来开始受到西方学者重视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就是这种批评者之一。
林毓生向我们介绍这一派的观点说:
“理性是重要的,但理性本身没有能力创造出完全合乎理性的东西来,要用理性的方式来了解理性本身究竟有多大本领,他们认为理性的能力是有限制的。因此不同于法国启蒙运动。后者用理性作为审查一切的标准,(文化、道德、思想、社会制度等等一切都必须合乎理性),不知道理性本身也要受审查,把理性提高到等于上帝的地步。 Hume 即认为道德并非理性所创造,而是经演化而来。社会制度亦然。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批评是,马克思通过黑格尔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它认为理性不但应该对文明加以重新设计,而且有本领设计出一整套美好无缺的文明。”这是“致命的自负”。”(林毓生:略谈西方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从五四到河殇》,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2 年)
顾准也持类似观点。
这种批评是有若干道理的。
的确,马克思主义亦有理性主义的成分。在谈及共产主义时,有理想化的色彩(“自由王国”“人类前期史的结束”)。另外,对理性的力量有过高的估计。
不过,马克思先于弗罗伊德而提出,人类的行为并非受理性支配,而是受生产方式和阶级利益的驱动,不过他们不自知,反而以为是意识形态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究竟生活于19世纪,他们的理性仍然带着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局限,尽管他们认为世界发展是辩证的,但又认为有着严格的铁的规律,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话说,是铁的必然性,或曰“社会发展是个自然史的过程”,某中社会形态必然要产生另一种社会形态,就向某种逻辑前提必然要得出某种逻辑结论一样,“人的努力至多是延缓或加速这种历史的过程而已。”
固然,马恩都不否认偶然性,但在他们的世界观中,确实没有为偶然性和人的自由选择提供足够的地盘(老年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发展的思想另当别论)。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仍未摆脱机械的、决定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又为列宁所继承、发展。
20世纪初,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给严格的因果律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自然科学的这些新成就并未被列宁所吸收。列宁只看到马赫的唯心论,但未看到马赫为新的世界观的准备所做的贡献—-这种贡献甚至启发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多次怀着感激之情提到马赫。
在列宁看来,社会规律也是被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人的活动为转移的。人只能认识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根本无选择可言。列宁多次使用“国家机器”这个概念,斯大林则进一步引申、展开这个概念。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机器顶端是共产党,其下是青年团、工会和妇联等群众组织,再下是广大的工人农民……。青年团、工会和妇联是传送带,带动了全社会的活动。这种观点完全不是把社会看做一个有机体,有它自身的规律,存在着向各种方向变化的可能。斯大林甚至认为,只要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机器,整个社会就会跟他走了,而每个人不过是这个庞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曾把文艺比做螺丝钉,毛泽东则赞扬雷锋是螺丝钉)。
马克思则在《资本轮》中严厉地批评资本家把工人当做机器的附件,当做齿轮。他认为这种工厂体制是摧残人性的,是异化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超越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他仍未摆脱牛顿自然观的影响。后一方面则被发展为苏联、中国极权主义社会组织的理论。毛泽东说过,要把全中国每一个人都放在一个组织里头。整个社会是一个金字塔,金字塔的最顶端便是领袖。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固然克服了18世纪理性主义的片面性,但又从18世纪的个人主义转到了全体主义(整体主义),他把国家看得高于个人,个人仅仅是绝对理性的工具。
当代共产主义则把个人看成共产主义的工具。人,就这样由目的变成了手段。这是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消极方面。
18世纪法国革命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中都产生了暴民政治和个人专制,这又违反了理性。
回过头来看,经验主义逐步改良的办法,反而显得更合乎理性,更使社会能稳定地进步。
(本文第一稿完成于1995年9月22日。次年7月7日,作者曾修订过,在解构和文字上有较大的改动,加了小标题,但没有完成。整理此稿时,我所做的工作是:删掉偶尔重复出现的引语,代之以“前面提到”等衔接词;将第一稿的开头和结尾截取过来作为本片的首尾,并以“缀语”来作为结尾一节的小标题,目的是提醒读者,这一小节是后缀上的——冯媛,2002年3月)
龍易◎大觀
Truth, Love and 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