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邢滔滔,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主任。研究领域为逻辑学和数学哲学。
4月21日,为庆祝清华大学111周年校庆和人文学院10周年院庆,由清华大学逻辑学联合研究中心主办的“清华逻辑学派的传承”校庆专题研讨会在人文楼举行。本文由叶凌远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修订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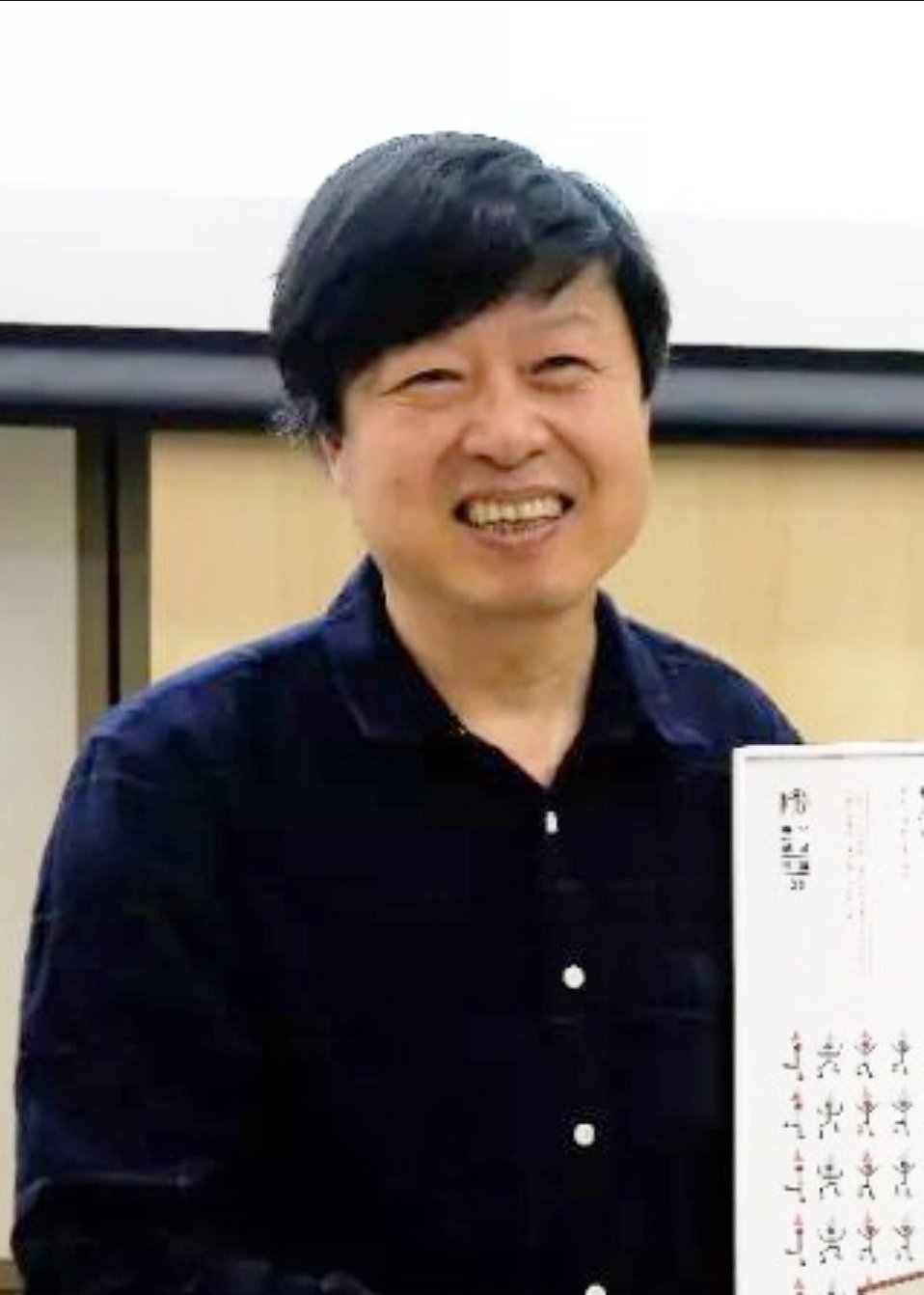
首先,祝贺清华和哲学系的生日,其次也感谢奋荣,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盛会。谈到清华的逻辑学派,我个人愿意做一点广义的理解。因为清华跟北大一直也不分家,地域上又都在中关村,再包括中科院,我们都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历史上,我们也是分分合合。如今,冯琦老师加入清华,也是合作的一个象征,希望将来我们能有更紧密的合作。
今天我主要想谈一些我本人跟王浩先生的些许交往。上世纪80年代,王浩在清华和北大都担任客座教授,做了多次演讲,我自己参加过的可能有三次吧。每次他来时都要看望自己的老师王宪钧先生。在这期间,从本科、硕士再到博士,我一直在北大。王宪钧先生师生关系融洽,已成为一个传统,我们好多课都是在王先生家里上的,也常在王先生家里吃饭。所以王浩在王宪钧先生家里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曾在座。我们学生还几次到勺园五号楼拜访过王浩。通过这些机会,我本人跟王浩先生有过一些交谈,第一个话题自然就是如何学逻辑,另外交谈中也涉及王浩自己的一些哲学观点和学术品味,这些跟我自己当时在写的论文有关。
关于逻辑学习,从王浩自己的经历来看,他去西南联大读数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数理逻辑。当时是王宪钧先生教他这门课,带他入门,用的课本是罗素的《数学原理》。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读希尔伯特和贝纳斯的《数学基础》。据王浩回忆,王宪钧先生从德国回到西南联大时,带来的是全新的逻辑学,超越了罗素的理论,而转入了哥德尔、希尔伯特、司寇伦等开创的新路,已经处于当时的前沿。所以王浩一进入逻辑,实际上就在这条新路上,他也一直很感念王宪钧先生的引导。
1945年王浩去哈佛跟随蒯因学习,但他关注的更多的是哥德尔、塔斯基等大家的思想,以及集合论、递归论等新的进展。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和蒯因的集合论系统相关的工作,但据他自己所言,这不是他思考的重点。他所关注的重点还是当时一些仍未解决的问题,思路承接的是哥德尔和塔斯基等人的工作。据他回忆,他有一次证明了一个数学系统能够证明自身的一致性,与哥德尔第二不完备定理相悖。他知道自己证明错了,但不知道错在哪里。他向罗瑟请教,讨论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针对我们当时课程开设情况,王浩建议说,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几何这些“老三论”已经不够了。要打好逻辑的基础,数学方面要学“新三论”,即实变函数、抽象代数和拓扑学。他还有一个建议很重要:不要以为自己起点低就不敢碰那些难的、新的问题。应该从阅读大师重要的论文入手,关注新的问题。不要等刀都磨好了再去砍柴,刀永远磨不好。
我们谈话的内容也涉及王浩基本的哲学立场,即 “Factualism”,现在翻译为“事实主义”,他自己称为实事求是的观点。对这种哲学立场有一个简单的描述:从我们已知的东西出发。我们要对我们已知的东西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知道什么比对于我们怎么知道的知道得更好。我们已经知道一些东西,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对于我们如何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因此在哲学上,我们不能从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出发,而要从我们已知的开始。所以他不主张传统的抽象的知识论(epistemology),而是建议一种具体的知识图谱学(epistemography),把已知的东西先展示出来,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那么,在数学哲学方面,事实主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先于任何哲学而朴素地接受数学知识,不要先怀疑。同时这意味着在字面上接受数学真理,不要像唯名论那样对数学命题做不恰当的翻译,曲解其意义。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当时数学哲学的“时代精神”,而王浩恰恰也反对“时髦”的哲学。对于当时的许多数学哲学工作,王浩是不屑一顾的。比如著名的本纳塞拉夫问题(The Benacerraf Problem),质问我们如何认识抽象的数学对象。按历史的因果的知识论,这的确成为一个问题。但在王浩看来,这是颠倒了顺序,我们应该先承认知道些什么,而怎么知道的是其次的问题。
所以在数学基础(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的研究中,王浩反对传统的三派划分,即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而选择一种五支的分法:
严格有穷主义
有穷主义
直觉主义
直谓主义
柏拉图主义
这种分法哥德尔也提到过,事实上哥德尔的区分比这五支还要精细,一共有八个派别。王浩支持这样一种划分,是因为它清晰地展示了数学知识的一个图谱,从上到下论域不断增加,方法不断复杂,相互之间不是只有分歧,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王浩主张一种融合主义或联结主义(connectivism)的观点:不要只见到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看见它们的联系;在态度上,不是要选边站队,而是要消解它们的分歧。一言以蔽之,要化冲突为互补。这或许和王浩先生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也有关系。
从整体上看,在这五支里面,直谓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承上启下,关系到两个“大跳跃”:向上对比直觉主义,有一个从潜无穷到实无穷的跳跃;向下对比柏拉图主义,有一个从直谓集合(在王浩的认识当中也就是可数集合)到任意集合(包含不可数集合)的跳跃。在数学上,它联结了构造主义和非构造主义;在哲学上,它联结了概念论和概念实在论。王浩自己相信且珍视概念性的知识(接受直谓主义),对概念的实在性问题暂作悬置。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排斥柏拉图主义,王浩自己曾说,如果像哥德尔一样感觉到接受概念的实在性对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数学理论是必要的,便可进一步接受柏拉图主义。数学和哲学在王浩这里是一体的。
在学术上,王浩推崇的是哲学-科学家。在他的著作《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爱因斯坦、哥德尔]都是伟大的哲学-科学家——这真正是一个稀有的品种,如今已经被精细的分工、剧烈的竞争、快出成绩的纠缠、对理性的不信任、流行的浮躁和对理想的拒斥所戕残,几近绝迹了。”这句话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
回到直谓主义。由于和我个人的论文相关,我向王浩问及他在50年代的直谓主义工作。前面提到,王浩的博士论文和蒯因的 NF 和 ML 系统相关,这与直谓主义也是有关的。直谓主义肇始于罗素的 PM,在外尔之后直谓主义大致发展为这样一个框架:即先接受自然数全体,再按照“恶性循环”原则(Vicious Circle Principle,VCP)逐层得到新的集合。直谓主义的问题是:在这个框架下我们能走多远?
王浩在1954年建立了一个直谓集合论系统 Σ,实际上描述的是哥德尔可构造宇宙 L 的一个前段,但用来标示阶的,不是古典序数,而是“先前可定义”的某种“可构造性序数”,由此做到“自动膨胀”(autonomous expansion)。王浩希望这样的自动膨胀能够远超 Church-Kleene 的递归序数,至少能涵盖通常的可数序数。这样,直谓主义才能起到上面所说的“联结”作用。但出乎王浩意料的是, Spector 在1955年证明了在 Σ 系统下的膨胀不会越出递归序数,这距离不可数集合尚有一个范围广大的空缺,也就是说, Σ 并不是王浩所设想的直谓主义的适当刻画。随后,王浩进一步主张引入广义归纳定义以超出自动膨胀:如果一归纳定义中出现的谓词是直谓的,则定义出的谓词也是直谓的,并且归纳定义在直谓序数的范围内迭次使用,其结果也是直谓的。但这样的归纳定义在形式上就违反了罗素的VCP,所以一般被认定为非直谓的。而且,Feferman 和 Schütte 基于Kreisel 的“可证性”设想证明,直谓序数的最小上界为 Γ0(一个递归序数),而这已成为当今关于直谓主义的标准结果。
但王浩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大直谓”想法,他如此“固执”的理由大致有如下三点:
首先是针对概念性知识的内在辩护:概念上我们已经清晰地理解了归纳定义的对象,这个理解并不依赖于归纳定义的非直谓表述,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现有归纳定义的形式化表述无法精确地刻画我们关于归纳定义的直观。
其次,真和知是相区别的:可定义性首先是有关于真的,应该与可认知或可证性相区别,而我们的目标是求概念之真,不单纯是可知。因此他坚持在直谓主义中采取“可定义性”的进路,不同意Kreisel“可证明性”的表述。
最后,还有一个以数学经验为基础的外在辩护:我们借归纳定义超越有穷,但不必越过可数,而且总是得到唯一的最小模型,而它正是标准模型,这在完全非直谓的情形里是做不到的。
在王浩的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哲学的理由直接用于数学,这也是他的观点不为正统观点所接受的一个原因。但王浩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二者本为一体:在这里,哲学问题是数学中直接诱导出来的,而要解决哲学问题必须要使用数学手段。在他看来,并不存在数学之上的所谓第一哲学,数学哲学就在数学之中,以数学体现出来。这与他的“哲学—科学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王浩的这项工作并没有进行下去。60年代之后,他基本放弃了直谓数学的工作,没有发展新的直谓系统,也没有像他许诺的一样对恶性循环原则提出新的表述,而把这些留待后人。我曾问他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也提到后来有人对他的直谓主义思想做过研究,询问他对这个研究的看法。但面对此类问题他都语焉不详,不愿意多讲;只是谈到直谓性问题非常复杂,例如哥德尔就曾把罗素的恶性循环原则细分成了三种表述,其强弱不同。我猜测,他一直苦于“看不清”直谓性概念,不能像戴德金对于数或图灵对于算法那样,把它“说清楚”。而说不清的,他宁肯不说。
然而,王浩的这项工作,逻辑学家们其实并未淡忘。96年纪念哥德尔的一次会议上,许多人(包括 Feferman 本人)都提到王浩的直谓主义想法,Charles Parsons 等甚至希望有人能继续做下去。此前我在德国见到 Lev Gordeev,他熟悉王浩的这项工作,也认为值得继续做下去。他评论道,王浩是哲学家,与罗素、希尔伯特和哥德尔是一类人,而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者。他的思想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能因为与流行的技术性结果相冲突就轻言其失败。
以上是我的一些回忆。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