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在魔鬼之眼的逼視下
披一片残破的风,漫步于孤寂的思想中,追寻人类悲欢的终极原因——这是我,一个诗者与哲人的宿命。预言世界末日本来属于先知的天职,然而,在这个庸人都很自信却又缺少先知的时代,我不得不作一个预言者。
在人类精神历史的长河中,关于世界末日的思考,是反复浮现的主题。不过,以往这个主题或者只表述遥远的预警,或者只意味着某种神秘信仰的悬设,或者只是人类想象力的一种畸形的延伸。而今天,我却在一个花香醉人的清晨,呼吸到世界末日的浓烈气息——那血腥的气息与现实之间,似乎只隔着一条窄窄的田间小路。
先知常用屠刀般锐利的理性切入思想;诗者和关注生命意义的哲人,却习惯于透过人们情感的震撼,凝视思想。因为,先知超越情感,而诗者和渴望采摘生命意义之花的哲人则超越理性的逻辑。正是两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引领我走进关于世界末日的思考。这两个互不相关的事件中,都有强烈的情感震撼,而且,都有魔鬼之眼,从苍穹之巅阴沉地俯视人类命运。
中国大西北,铁黑色的戈壁滩和枯骨般苍白的沙漠横亘万里。那种荒凉的色调是对生命的冷酷否定。不过,在戈壁或大漠间,孤独的旅人常常会猝然发现一只仿佛青铜雕成的蜥蜴,正痴迷地盯着一朵石缝间摇曳的小花,并伸出艳红的长舌,舔食金色花蕊中的露珠——露珠晶莹得宛似天使的眼泪——那一刻,人的灵魂会在生命的感动中融化为一首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一位维吾尔族牧羊人为找寻被黑风暴吹散的羊群,走过戈壁,来到大漠的边缘。荒凉的寂静本就是牧羊人的伴侣,可是,他却突然感到一阵从骨头里渗出的死寂,好像自己的心瞬间变成冰冷的灰烬,随风飘逝在死去的时间中。那种恐怖的寂静之上似乎冻结著永恒,然而,永恒也有尽头。就在永恒的终结处,茫茫的沙漠犹如大海的怒涛,汹涌澎湃;一轮巨大的浴血的太阳突然从震荡的沙漠中隆起。
牧羊人的眼球似乎被强光点燃了,他身边的十几只羊身上腾起猩红的火焰。铁铸的戈壁发出惨厉的呼嗥,裂开道道巨大的缝隙。牧羊人像被吞噬一样,坠入大地的裂痕间。仰视中,牧羊人看到,燃烧的狂风从裂痕上呼啸而过,铁黑色的裂痕边缘被烧成暗紫色;那轮仿佛从地狱里涌起的太阳,急速翻腾著,升向天空。牧羊人觉得,那是一只充血的魔鬼的独眼,凶狠地向他瞪视。
后来,黑云笼罩了苍天和大地,牧羊人爬出地裂的缝隙,像一缕受伤的风,飘回家乡。他把可怕的经历讲述给自己的亲友,不久就死去了。他的死亡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他的身体溃烂,皮和肉一块块剥落,似乎被无形的铁爪撕掉了;臝露出的骨骼呈现出暗黑色,犹如生锈的铁。死前,牧羊人相信,他是受到了那轮从地狱中涌起的太阳,即那只魔鬼独眼的诅咒;死后,牧羊人溃烂的眼睛仍然瞪视着这个世界,仿佛永远不会愈合的恐惧。
当我在一个没有星月的暗夜中听到别人转述的这个事件时,我关注的并不是维吾尔牧羊人个人的悲惨经历,也不是中国大西北核爆炸试验场地周围几百万人长期受到核污染戕害的社会悲剧,因为,那一刻,一个哲理如同有毒的棘刺猝然刺入我的眼球。在流血的黑暗中,我看到那个哲理狰狞的笑容;他预言人类前所未有的大劫难和世界的末日。
“创造和毁灭世界的能量本属于上帝,当具有原罪的人理解并控制了这种能量之后,属于上帝的能量就将转化为魔鬼对人类的诅咒;它预言世界浴火自焚的末日。”——狰狞的哲理如是说。
在西方宗教信念中,有一个意蕴深长的传说:一群古巴比伦的石匠试图修建通天之塔;上帝通过变化石匠的语言,使他们难以互相沟通,从而阻止了修建通天塔的努力。
我无暇思考那群已经湮灭于时间深处的石匠究竟为什么要修建通天塔——是为了获得本属于上帝的创造与毁灭命运的能量,还是为了在永恒和无限的绝顶之上同上帝对话,或者是想要使人的智慧成为宇宙的绝对精神。我也厌倦于去理解上帝阻止修建通天塔的真实理由——是认为需要永远赎罪的人类没有资格到达时-空的极致之处,还是怕人类成为宇宙绝对精神的僭主,并自称“上帝”,或者出于大爱之意,不愿人类从苍穹之巅盗取能够毁灭世界的能量,用于尘世的利益争夺,从而自戕。但是,我知道,当代人类已经筑成通天之塔,这座通天之塔就叫作科学理性。我也清晰地看到——清晰是因为站在尘世之上俯视——通过科学理性,人类只从上帝的圣殿中盗取了毁灭世界的能量,却没有获得宇宙绝对精神对生命意义的祝福,相反,这是一个离精神已经越来越远,并像尾巴被点着的鼠群疯狂奔向物性贪欲的时代;人类似乎急不可待地渴望让自己的命运退回物性的黑暗中,而对于精神价值的厌倦,甚至仇恨,似乎被奉为时代的主题。
核烈焰的壮丽逻辑在宇宙精神的意境中本来属于创生的能量,因为,他是太阳炽烈的灵魂,而太阳创造了生命存在的条件,也创造了人类的命运。然而,人类以科学理性的名义控制了本属于上帝的能量之后,却把核烈燄的逻辑由生命的创生者转化为世界的可能的毁灭者;当代人类早已经完成毁灭地球和人类命运的能量积蓄,只在等待某个历史进程把世界推上毁灭的断头台。现在,这个历史进程踏着时间的血淋淋的伤痕,正在走进现实。
诸多关于二零一二年人类劫难或者世界末日的流言传播已久。那些流言不过是一个由于缺乏理想主义而过分无聊的时代,人们试图从毁灭的恐怖中寻求刺激的无聊努力。流言是无聊者的无聊的虚构,真实的则是,中共暴政将在二零一二年百花凋残、黄叶漫天飘零的时刻,进行一次权力全面交接。而这个事件将拉开世界末日大劫难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构成毛泽东展现中共极权恐怖的经典时期。二零一二年全面接控中共最高权力的一代人,主体是毛泽东式政治恐怖的“冲锋队”,即“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红卫兵”;毛泽东肉体死了,他的政治灵魂却活在这批人的心中。他们走上权力之巅,不仅将继承邓小平时期的权力极度腐败的遗产,也将复活毛泽东的世界性野心——那是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现代经典表述,即共产主义控制人类命运的野心。中国将因此进入万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
纵观历史,现代之前还从来没有过极权政治控驭毁灭世界能量的先例,所以,人类的命运还能在跌宕起伏中艰难地趋向自由。试想,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和十字军,或者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如果得到核烈燄逻辑的祝福,自由还能成为人类命运的趋势吗。现在,魔鬼把开启世界毁灭之门的核烈焰的钥匙交给了中共极权体制,而且,中共的国家能量——至少它控制了十五亿政治奴隶,乃是中世纪罗马教廷和当年的纳粹德国根本无法相比的。更何况疯狂膨胀的经济实力,已经合乎专制政治天性地迅速转化为全球极权扩张的政治意志。
上述状况所预言的人类大劫难可以令太阳都由于恐惧不寒而栗,然而,人类却在诸如“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的希望之星”一类豪华的谎言中,搂抱着幻想走向命运的断头台——谎言是由中共收买或者豢养的学者、文人、伪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制造出来的,但是,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当代这样厌恶真相,渴望甚至迷恋于谎言;难道人类除了相信谎言再也没有任何出路了吗?
我书写预言之书,目的之一就是要摘下挂在苍穹上的晚霞般绚丽的谎言,让人类看到,黑暗天幕上的魔鬼之眼正在逼视人类的命运。那只魔鬼的眼睛里,燃烧着毁灭的烈燄;太阳似乎都将在魔鬼之眼的烈焰中像冰块一样融化,那或许是因为,魔鬼之眼离这个世界比太阳更近,近得如同抵在咽喉上的尖刀。
另一个引领我走向世界末日思索的事件,在起点处似乎也只与个人悲剧有关。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机中,一位富有的女人由于金融投机失败,云峰一样高耸在天际的财富,以及想成为澳洲首富的野心转瞬间烟消云散。这个女人原本欲望沸腾的眼睛变得像骷髅眼眶的空洞,凝结著死亡的茫然。她用手凶狠地抽打自己的脸,撕下一缕缕干枯的头发;她以头撞墙,仿佛想绝望地撞开黑牢的铁门——她的心因为被金钱抛弃而破碎,以至于她试图用肉体的自虐来掩盖心碎的疼痛。
冷冷地看着这个濒临破产的女人,我没有一丝同情,更不屑于给她安慰。我高贵的安慰只能给予在真诚的情感悲剧中怒放的痛苦,而同由于失去金钱破碎的心无缘。
这个曾经富有的女人终于因为失恋于金钱而自杀,然后又被救活。她讲述了被死亡亲吻的时刻呈现出的景象:滚滚红尘中,人都变成物欲的火焰之鞭抽击下的饿鬼,发出能撕裂铁石的惨痛呼嗥,互相疯狂残杀,贪婪地吸食别人的血泪,从别人的眼眶或者胸膛里剜出眼球或者心……。猩红的天空中,一只魔鬼的独眼充满恶意的嘲弄,斜视著为物欲而疯狂的尘世,异化为地狱的尘世。这个曾经富有的女人震惊地发现,那只魔鬼的独眼竟然就是印在一美元钞票背面的“光明独眼”——在古埃及的信仰中,“光明独眼”是象征太阳的图腾。
本来表述太阳之神的“光明独眼”,由于同金钱结合,便异化为物欲的魔鬼之眼。这就如同作为太阳之魂的核烈燄的逻辑一旦被极权者控制,便从上帝创造生命的能量,转化为魔鬼毁灭世界的能量。上述两种异化过程都归结于魔鬼对人类命运的诅咒,而不同之处在于,魔鬼之眼中燃烧的核烈燄,是人类踏着科学理性的通天之塔从上帝的圣殿中窃取的;魔鬼之眼中燃烧的物性贪婪,则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的宿命。
那位被金钱抛弃而心碎的女人,在濒死的体验中受到魔鬼之眼的轻蔑斜视。不过,她的个人悲欢并不值得作为哲学思考的课题。因为,迷恋于金钱而不是爱情的女人,同贪婪于专制权力的男人一样,本质上都属于形而下的粗糙、污秽的存在。然而,这是一个疯狂的物性贪婪主宰的时代,是人们争先恐后把心灵出卖给金钱的时代。维吾尔族牧羊人受到核烈燄的魔鬼之眼的诅咒而肉体溃烂;那个曾经富有的女人则受到美钞上的魔鬼之眼的诅咒而精神溃烂——这种精神的溃烂同时是属于时代的,是人类命运的精神溃烂;时代和人类命运的悲剧主题,当然应当受到哲学的关注。
宇宙中比永恒和无限更伟大的事件,便是人以心灵的名义从混沌中脱颖而出,用精神主体之光照亮自然的黑暗,使现象世界清晰地呈现出来。茫茫宇宙间,地球不过是一个趋于零的点;在物质存在形式的意义上,附着于地球上的人类,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不过,人类却又能够把浩瀚的宇宙当作思考的客体,从而使自己获得认识主体的高贵资格,成为宇宙中的精神之花和自由的理解者。这全在于人本质是物性之上的心灵的存在。人的命运本质上是自然本能过程之上的文化存在——人不是基于物性,而基于精神,才高于兽性和万物,才获得理解并创造美、自由的资格,才有权利思索上帝才配思索的主题,即永恒和无限。
但是,当代主流的生活方式却证明,人类决心放弃以往的全部精神努力,并把物欲视为生命意义的极致。物性贪婪丰盈如满月,精神的星群却黯然湮灭。人类正以物性贪欲的名义,回归物性的黑暗。人类正在物化,命运正在物欲中腐烂。肯定物性,否定精神,便意味否定人的本质;肯定物欲,否定心灵,便意味否定人的意义,并从根本上否定生命的幸福感。因为,幸福是心灵的体验,而不是物性的表述。当精神的太阳沉落之后,自然的地平线上不会涌起绚烂的晚霞,而只会有物性的永恒黑暗再次漫过苍天和大地。
物性贪欲是生命的原罪;追求物性贪欲进行的争夺是尘世间的万恶之源。如何用精神的力量阻止物性贪欲主导人类命运,构成宗教圣者和相信理想主义的哲人、诗者的思想主题。那是同人类万年精神史相随相伴的主题。现在,人类却扯断使自己的命运同宇宙真理相接的心灵的藤蔓,走入精神毁灭的绝境死地。我不能确定,魔鬼独眼中物欲的火焰熔铸出的屠刀,将在哪个清晨或者黄昏落下,斩断人类的命运,不过,我可以确定,道德良知和理想主义的堤坝崩溃之后,从人类生命深处奔涌而出的物欲的狂涛怒潮,必定把历史冲向世界末日。
当代,从西方到东方,从政客到文人,从珠光宝气的华尔街富豪到蝇群萦绕的印度乞丐,从扭捏作态、搔首弄姿的演艺明星到中国的千万妓女,从和尚尼姑到海盗或者教授,遍观世界,各色人等,几乎无一例外在为金钱而焦虑疯狂。似乎只有恐怖主义者还在坚守理想主义,只不过,无辜者的死亡又使属于恐怖主义者的理想变成罪恶。
连上帝都会因之而困惑之处更在于,民主政治与极权专制本应冰碳不能共存,水火无法相容,现在竟然也能以物欲的名义融成同一滴肮脏的血——美国和中共宣布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便是例证之一。尽管如此,也不能不承认,风靡全球的物欲狂潮最初源起美欧的生活方式,而这种表述时代个性的生活方式,是在自由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自由没有创造出丰饶的审美激情和华贵的思想,却为散发出浓烈腐臭气息的物欲生活方式作证,这说明自由病了,而且病入膏肓——“自由”病了,这才是这个时代最致命的精神危机。
自由是人类的拯救者;理解自由是最神圣的思想事业,每一扇伟大的历史时代之门,都是由对于自由的再理解所开启。以往的历史中,无论命运处于怎样凶险危难的境地,都有以自由的名义书写的理想主义旗帜,引导人类走向未来。自由曾经是拯救者。可是,现在自由病了,拯救者首先呼唤拯救。人类由此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拯救自由需要思想来自天启的圣徒、哲人和诗者,但是,在一个俗不可耐的庸人都比上帝还要自信的时代,面对形而下的蠢物白痴都敢嘲笑理想主义者的情势,即便有从宇宙精神中获得思想灵感的天纵英才,也只能是孤独者;自由需要拯救,而蠕蠕如虫蚁的庸众却愿意让自由随他们肮脏的肉体和本能一起慢慢腐烂。
源自中共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连太阳都被烧焦的炽烈的物性贪欲——这是两只逼视当代人类的魔鬼之眼,然而,很少有智者敢于同魔鬼之眼作英雄的对视。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试图通过粗俗本能的狂欢,遮掩空虚的精神上绽裂的焦虑与恐惧:那似乎是对物化的生命本身的恐惧,以及对世界末日的直觉产生的焦虑。
我书写预言之书,不是为了表述不可改变的末日的宿命,也不是为了把绝望之钉钉入人类的眼睛。因为,我厌恶宿命,并渴望注视绝望之后的原野。
我书写预言之书,是为了踏过世界末日的宿命的锋刃,撞向一个属于心灵时代的晨钟;在那个时代中,高贵的自由人将表述对审美激情的热恋,对社会正义的理解。
苍天和大地告诉我,即使能用炽烈的英雄之心点燃死灰或者顽石,也难于用理想主义感动只相信物性贪欲的人类。但是,我仍然要走上黑暗的时代之巅,用心灵的火焰亲吻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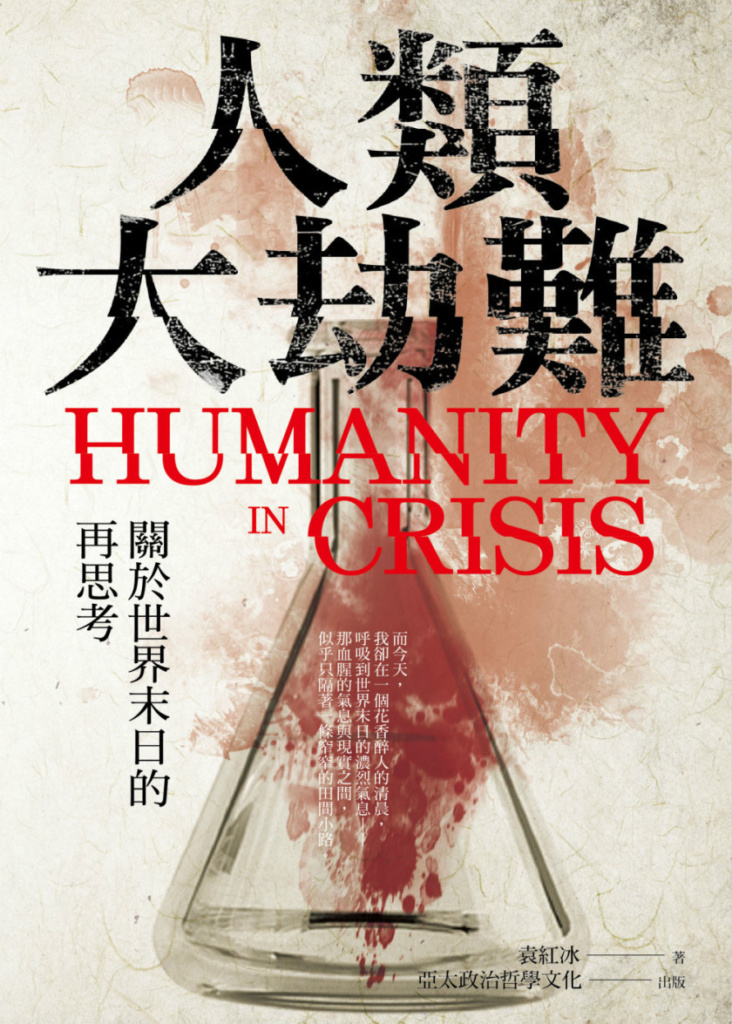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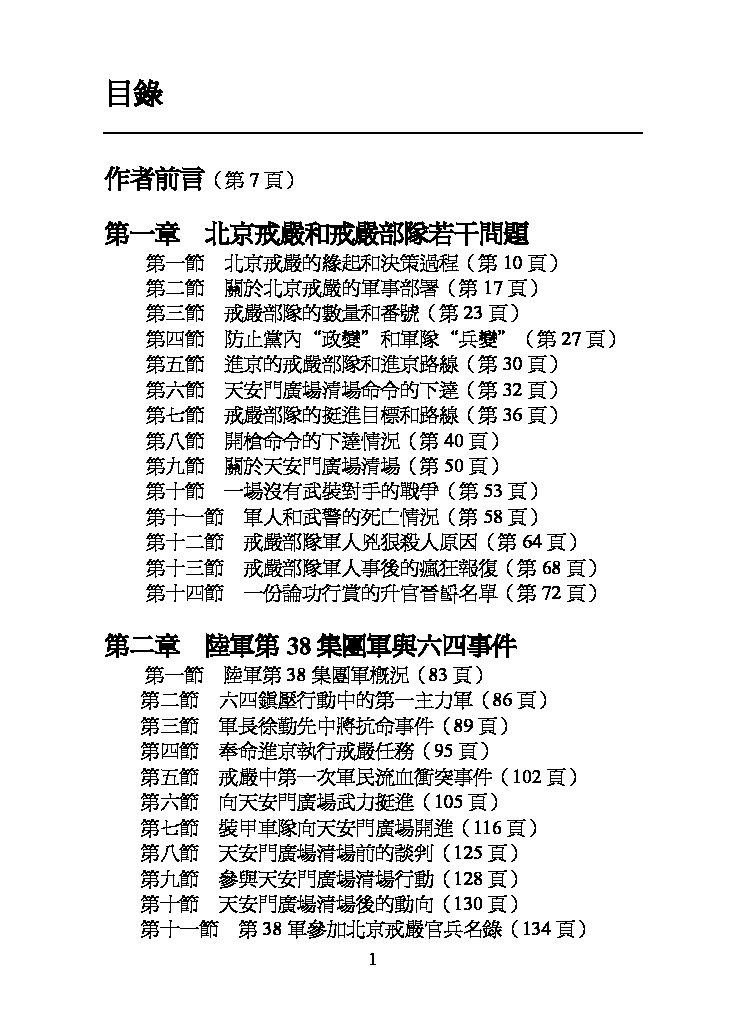



,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召开夏季常务会.jpg)
